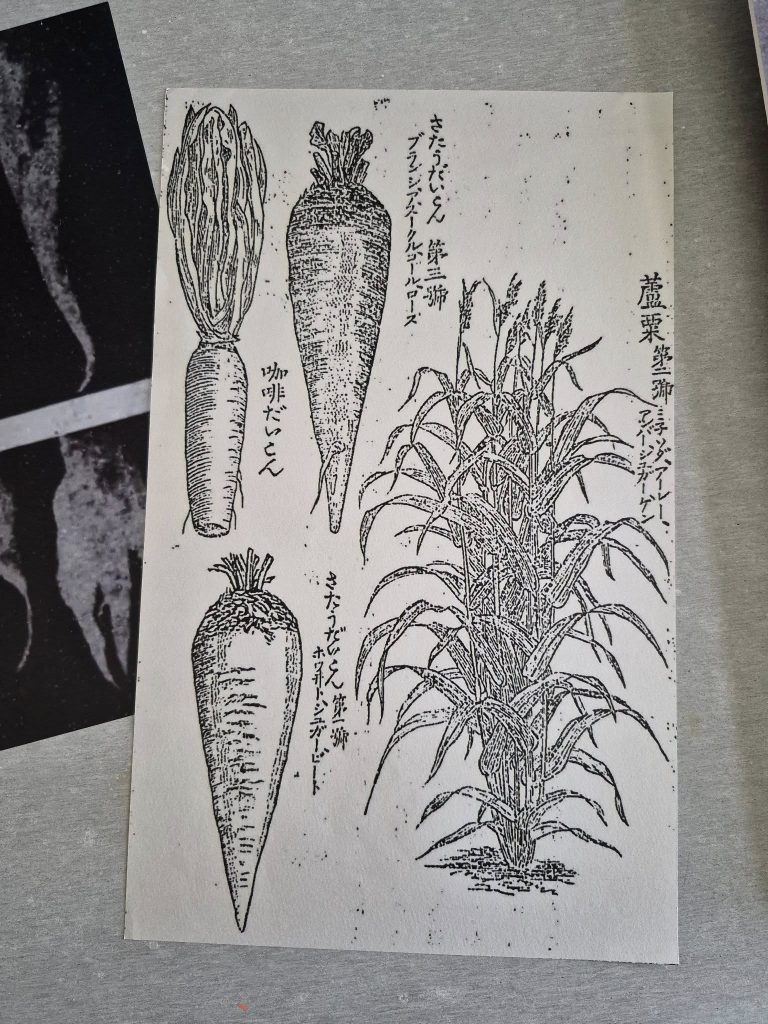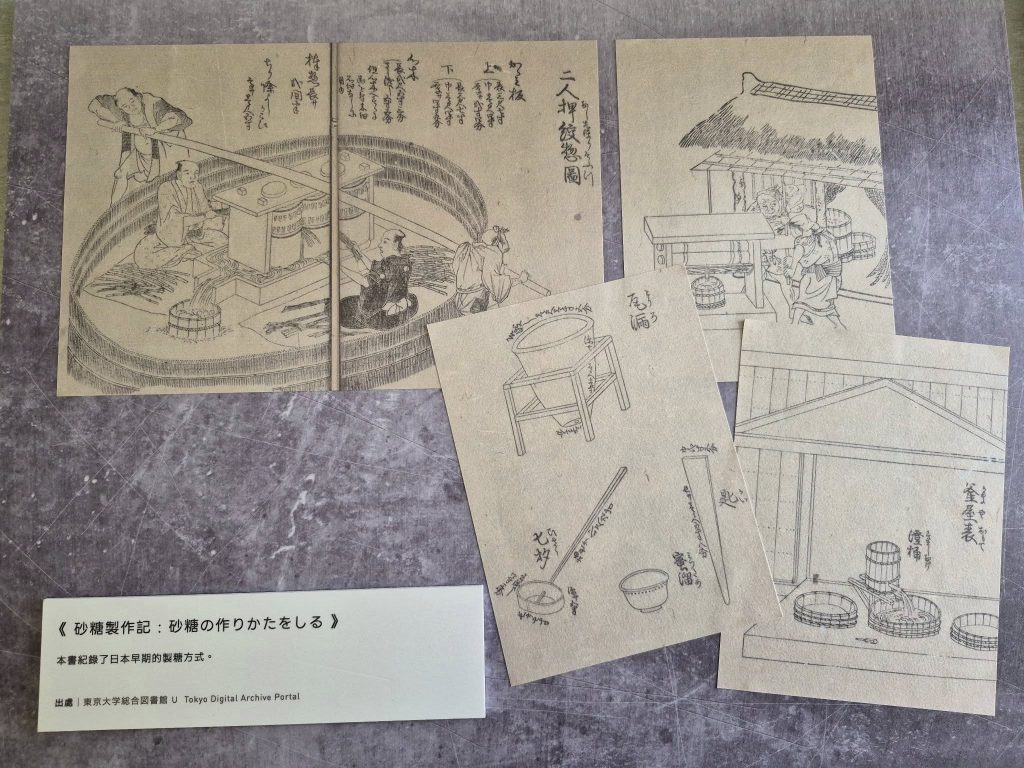在喀什米爾的 Royal Sweets Point,櫃檯上陳列著一盤盤閃著光澤的甜點。當地人推薦一定要試試 Cham Cham!

Cham Cham 起源於孟加拉,它的誕生並不是「煮奶」或「烤餅」那麼簡單,而是一段精密又細膩的轉化過程。先將牛奶加熱、滴入檸檬汁或醋,使蛋白質分離,這一步叫做「curdling」。過濾後留下的凝乳就是 chhena。混入少量的粗麵粉與小蘇打,讓它的結構更穩定、彈性更好,也能在煮糖漿時不散開。小心地將橢圓形的奶酪糰放入滾沸的糖漿中(加上豆蔻或藏紅花調香),高溫壓力讓它膨脹、吸糖,同時保持柔韌。
在喀什米爾,Cham Cham 通常呈現淡黃或乳白色。糖漿裡多會添入當地名產藏紅花(saffron),淡淡花香與奶香交織,使甜味更內斂。這樣的甜點,往往出現在節慶、婚禮、與待客茶席上。對當地人而言,它不只是糖與奶的組合,而是一種「款待」與「祝福」的形式。不張揚的味道,卻在喀什米爾的冷空氣裡慢慢滲開。它的精神「用有限原料做出層次甜味」,其實和台式點心的思維很接近。
無論是喀什米爾的糖漿香,還是台灣蒸籠裡的米香,背後都藏著同樣的心意:用最樸實的原料,去成全生活裡的一點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