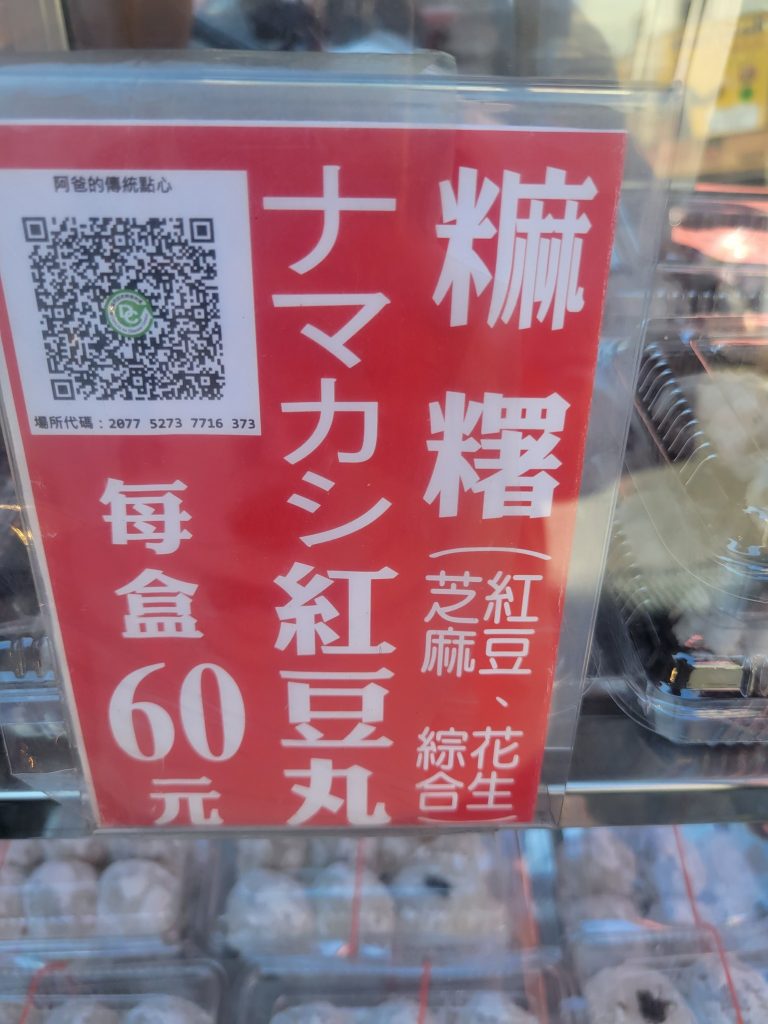印度甜點 Rasmalai(奶豆腐球),源自東印度的 孟加拉地區,是經典甜點 Rasgulla(糖水奶豆腐球) 的延伸版本。

兩者都以 Chhena(奶豆腐) 為主角——將牛奶加酸凝結成柔軟凝乳,手揉成球,再放入糖水中煮,使其膨脹、吸飽甜味。
十九世紀中葉,孟加拉甜點師 Nobin Chandra Das 改良傳統作法,成功做出質地更細緻、入口即化的 Rasgulla。
之後,他的兒子 K.C. Das 將這款甜點推向全印度市場,並以罐裝形式販售,讓 Rasgulla 成為印度甜點文化的代表之一。
在此基礎上,K.C. Das 家族 進一步發展出更濃郁柔滑的版本──Rasmalai。
「Rasmalai」一詞由兩個字組成:
Ras 意為「甜汁」
Malai 意為「奶油」或「濃縮乳脂」
象徵被奶香包裹的柔軟甜味。
他們將 Rasgulla 從糖水中撈出,改以煮過的牛奶與香料浸泡。這道香料奶液以 藏紅花和小荳蔻調香,再灑上杏仁與開心果碎,冷藏後食用。讓奶香取代了糖水的清甜,使甜味更圓潤,也更具層次。
 Rasgulla 的發明之爭
Rasgulla 的發明之爭
關於 Rasgulla 的起源,長期以來在印度東部形成了兩種說法——就像台灣人爭論「珍珠奶茶到底是誰發明的」,這也是一場甜味的文化競賽。
奧里薩邦(Odisha) 認為,早在孟加拉人宣稱之前,當地女神 Jagannath 神廟的祭品中就已有類似糖水奶球,名為 Pahala Rasgulla。這項供奉傳統可追溯至十五、十六世紀,被視為地方信仰的一部分。2019 年,奧里薩邦政府成功取得「Odisha Rasgulla」的地理標誌(GI tag)登記。
而 西孟加拉邦(West Bengal) 則主張,現代製法的 Rasgulla 源自 Nobin Chandra Das 於 1868 年的創製。2017 年,孟加拉政府也獲得「Banglar Rasogolla」的 GI 登記,正式確立其版本的地位。
這場爭議持續數十年,直到兩地各自取得地理標誌登記,才算暫告一段落,也讓這顆小小的甜球,成為印度飲食史上最具代表性的「文化象徵」。
如今,Rasmalai 在印度、孟加拉與巴基斯坦各地皆能見到,常作為婚宴與節慶的甜品,象徵「幸福與祝福」。
它的誕生,也標誌著南亞甜點從糖水到乳香的轉變。讓甜味不再只是糖的濃度,而是一段凝結信仰、時間與文化的香氣。